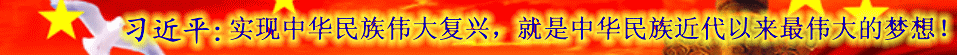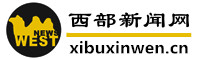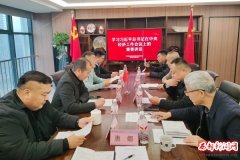编者按:4月10日下午,纪录片《三秦珍档 奋斗足迹》摄制团队在西北大学陕西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采访了中心理事长桂维民。理事长围绕书籍《国家156项工程在陕西企业纪实》编纂前后的经历,分享了在参与陕西“156工业遗产”保护行动中的所思所感。
《三秦珍档 奋斗足迹》由陕西省档案局、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委军民融合办、《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共同出品,节目主要聚焦于“一五时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中落地陕西的24个项目,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档案,采用口述档案的形式进行拍摄,生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那段洋溢着奋斗精神与梦想的历史。


▲陕西(西北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桂维民接受纪录片《三秦珍档 奋斗足迹》摄制团队的采访(摄影/徐昕蕾)
城市如同一本不停翻页的书。页脚的灰尘,是时间留下的注解;高楼之间锈蚀的厂房,是一段不该被跳读的段落。
人们急于向前,而桂维民却选择停留。他向过去致意,不是出于怀旧,而是一种更坚决的现实主义——一种对工业文明根脉的信仰。


记忆的深井
他不是历史学家,却以一种历史学家的姿态出现。他不是建筑师,却想为工业时代的残骸搭建一座座精神的穹顶。
“我是50年代生人。”桂维民开口,总是平缓的,但语气里有种长久背负之人才能带出的厚重。他谈到“西迁”的那一代人时,语气悠长,那是一代人将国家命运内化为自身荣辱的年代,是“工业”成为信仰的年代。
156项工程,如今听来略显遥远的数字,其实是一组力量的符号,是共和国工业化原点的坐标图。而陕西——这个如今在全国发展版图中略显沉默的省份,当年却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落地最密集的地区。


▲1958年,莫斯科石油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同学一起研讨。
在煤炭、电力、电子、兵器、航空、船舶等重要工业制造领域,创造了当时诸多个亚洲和中国的第一……它们从地图上的点,变成了时代里实实在在的砝码。
而当2016年的城市改造工程悄然展开,“幸福林带”计划开始拆除一批旧厂房时,桂维民感到了一种无声的紧迫。他说,那不是拆除,那是在抹去。他意识到,再不行动,记忆就将被彻底裹挟进泥土与混凝土的混流中。
他选择了行动。


▲召开《国家156项工程在陕西企业纪实》出版座谈会。
他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拍桌,而是写信——给省委、省政府提交了一份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和策划书。第二个动作,是在西北大学召集学者和专家,谈保护,谈工业记忆,谈工业时代的情怀与价值。座谈会最后商定,要做三件事:拍一部纪录片,建一个博物馆,出一本书。
文字的重量
书,是一切记忆最安静的承载方式。
但也正因安静,才需要更深的敬畏。
《国家156项工程在陕西企业纪实》,110万字,五年时间,数百张照片,不只是纸张上排列的知识与资料,更像是从废墟中打捞出的遗言,是对沉默年代一次迟来的礼赞。


▲1958年底第一辆用苏联提供的配件生产的t-54a坦克下线。
桂维民并没有把自己当编者,他更像一名中转站的工人,把过去搬运到现在。
他说,最难的不是撰写,而是“识别”——在一堆尘封的档案中甄别哪些是真实的、可信的、能承担起历史重量的。
为此,他们一层层递交审核,从企业到档案馆,从地方志到党史研究机构,像做一次繁琐的手术。


▲1959年第3期《人民画报》,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百万吨级炼油企业——兰州炼油厂。该项目为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这份书稿里,不只有铁与火的工业数据,还有人的故事。他提到吴玉宝,一个来自上海的普通工人,为修建宝成铁路主动请缨,火车开动那一刻,车厢里哭声一片,而几小时后,哭声变成了笑声——因为他们知道,目的地不是远方,而是理想的现场。
还有贾棠荣,一位化工专家,说起当年钱学森来厂里指导时的三句话时,眼里仍有光。那是科研人员为国铸剑的时刻,固体火箭推进剂的突破,让中国的“两弹一星”提速了整整两年。


▲2016年9月,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201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迎来通车60周年。2018年1月,入选中国第一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这些叙述,不属于文学,却饱含文学性。他们不是为了抒情而存在,而是证明:国家不仅由制度构建,也由记忆支撑。
空间的叙事
工业遗产保护在当下中国常常陷入两难:是留住过去,还是让位未来?桂维民说:“我们做的,不是守旧,而是转译。”这种“转译”不是语言上的翻译,而是空间、时间与情感的再造。
铜川的王石凹煤矿,是他最喜欢讲的案例。


▲前苏联援建的王石凹煤矿是国家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之一。
这里曾是“共和国煤炭工业长子”,而如今已然停产。当矿井沉默,城市是否还记得它的声音?
答案是:让它“重新说话”。
这片矿区被重新规划,煤井变成展厅,废弃的苏式单边楼成了研究中苏合作工业遗迹的活化样本,甚至连运输用的火车头都被打造成了餐厅。他不满足于“修旧如旧”,他想让这些工业符号,在数字时代有一种全新的叙事结构。


▲王石凹煤矿工业遗址公园
这种保护,不再是小心翼翼地供奉,而是让历史变得可亲、可感、可体验。人们在展馆中行走,穿过井道模型、听矿工口述,孩子们用VR设备“下井”,老人们在茶歇区讲述他们“当年在井下”的故事。
记忆不再是尘封的展品,而是活的语言,是当代语境下的续章。
他介绍说,王石凹提出了一种“协同创新机制”——不是单靠政府,也不完全商业化,而是“政府+企业+村集体”共治。


▲运煤机车无言的诉说着昔日工业文明的历史荣誉。
只有当遗产真正进入生活场景,才不会变成被遗忘的标本。铜川,也正在从资源枯竭的工业城市,转身为生态与文化共生的新城市模型。
从他者到我们
在这段关于遗产、记忆与未来的对话中,桂维民反复说,自己并不是主角。
然而,他却像一个持灯者,在工业时代与今天之间搭起一座桥。他不谈“感动”,更少说“使命”,但他的话语中自带一种“必须做”的坚定。
这份坚定,不是来自某种道德高度,而是他对一段时代有着近乎朴素的尊敬。


▲寻找“156项工程”:西安韩森寨工业区的前世今生。
156工程,不只是一页宏大叙事里的注脚,它曾是成千上万普通人生活的起点、信仰的支点与苦难的交汇点。如今他们老去、散去。
而桂维民为他们说了话,写了书,将来还要建个馆。
历史不会开口,但它会留下沉默的遗址。正是这些人,让沉默的遗址重新发声。他们用双手打捞回记忆的闪光点,也照亮我们理解国家、理解城市、理解父辈的一种路径。


▲预计改造后的老工业区
而当我们走进那些旧厂房时,也许会突然明白,所谓“新时代的叙事光芒”,其实不是新造的,而是我们终于学会读懂那些旧的。